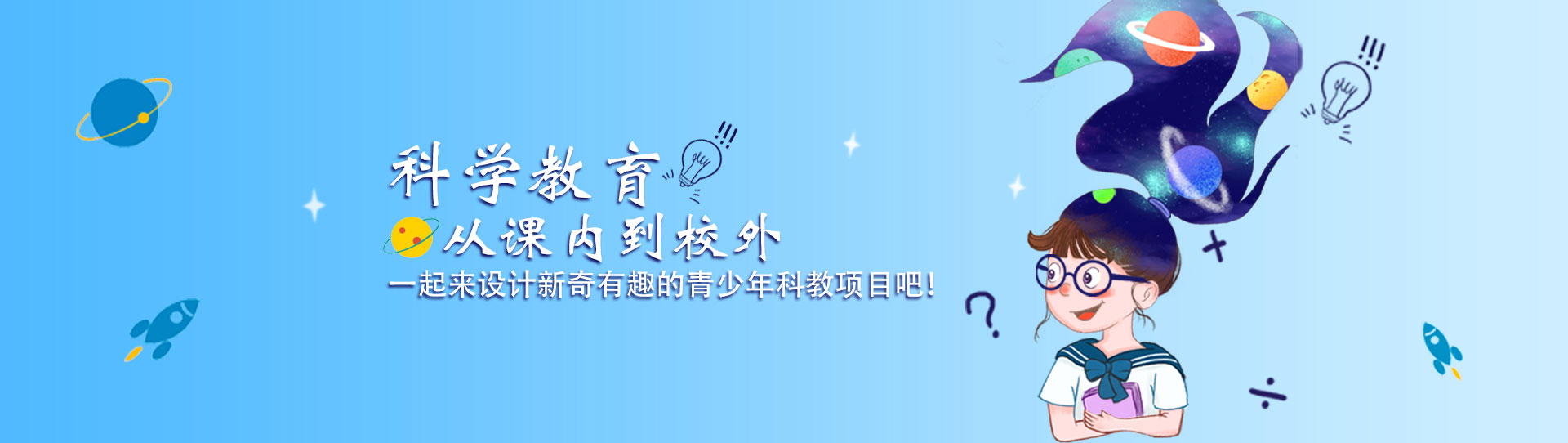寒露节一到,季风就换了花样。不再黏着人吹,而是带着飒飒的清冽,从北边的伏牛山一路南下,把老家羊山、磨山、塔子山的三山坳里吹个透心凉,这是早年的记忆。
高中毕业那年,寒露日,天还没亮,生产队的钟声就响了。那 “ 当!当!当! ” 的响声在晨雾里震荡着整个沉睡的村庄。
我赶忙穿衣起床洗漱,妈妈从门后取下一盏旧马灯,玻璃罩子擦得锃亮,火苗不断的上下跳跃着,把界墙上那张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年画照得通红。
“今日寒露,该种麦了。”妈妈一边小声说着,一边往旧马灯里添了一些煤油。煤油刺鼻味混着早晨的湿气,凝成了我农村记忆里寒露节特有的味道。
妈妈拾掇完旧马灯,递到我手中说:“听队长的话,今天就跟着你四伯学犁地、学耩地。不要嫌脏,要有眼色,麻利一点,学种地是咱农村人吃饭的门路。”
听完妈妈温情的嘱咐,我提着马灯,大步流星赶往村头的牛棚。此时,四伯早把牛棚外犁地、耙地、耩地的一套农具放到了牛车上。
四伯见我来到,笑着招呼我去牛棚牵牛。来到牛棚,两头黄牛老犍正卧在地上反刍。见我眼生,忽的站起,鼻孔里喷出两股白气,眼晴瞪得铜铃一般,警惕地审视着我。看着认生的黄牛老犍,我赶忙喊四伯过来解围。
四伯进棚拍拍两头老犍的脖子,把牛绳递给我,温情地说:“老伙计,不要认生,跟着这后生走,老实一点,请你出力的时候到了。”
两头老犍好像听懂了什么,迈着四蹄,跟我走向棚外,仰着头,同时“哞了一声,惊飞了老槐树上栖息的一群麻雀。
天还不明,黎明前无月的天更加黑暗。我提着旧马灯在前引路,四伯赶着牛车紧随后边,落下一路牛铃声。
一刻工夫,到达田地,我们卸下农具,给两头老犍换上犁套,四伯就开始给我示范犁地的技艺。
犁地是一门种地技术活,四伯是生产队几十年的老牛把式了。他一边犁地,一边告诉我:“犁地不看牛,看的是犁沟,右手扬牛鞭,左手轻轻抖。”
两头黄牛老犍在我马灯的照明下,并肩拉犁向前,四伯眼望犁沟,左手轻松掌控犁把,犁铧入土的深浅恰到好处,新翻的泥土像一波波浪花卷向右边。
犁翻的泥土散发着一股股腻腥气,不是作家们文章里所写的那种泥土芳香。那种味道很特别,是蛰伏一个夏季的泥土被翻醒后的乏味,混着露水和腐草植物根须的气息。
犁地是寒露耩麦的头道工序,犁过的土地还粗糙着,大大小小的坷垃块子散了满地,这就需要用耙齿将新犁的土地耙耘。
耙是一种传统农具,长方形的木框框,两排铁齿有半尺多长。两头牛拉着,四伯站在上边,像驾驶着无底无顶木船在土浪里航行。四伯拉着牛缰绳,两腿挺直,腰杆挺直,时而单脚减压,时而双脚加重,耙齿耘过之处,土块渐渐细碎。
四伯嘴里叼着旱烟袋,一边叭啧着烟嘴,一边告诉我:“耙地要趁墒,早了粘耙,晚了难碎。”
晨曦里,牛走着,耙耘着,一趟趟,一遍遍,田地被耙耘得平整如画,只有很少的顽固坷拉零星蹶在地面上。
天亮了,田地里便热闹起来,妇女队长王二婶带着一群女社员,提着榔头赶来了。王二婶是个人,她扬起榔头,带头唱起打坷拉歌。“塔子山上太阳升呀嘿,彩霞万丈满天飞呀嘿,姐妹们用力打坷垃呀,大坷垃碎成芝麻面呀嘿……”
妇女们歌声声震田野,犹如天籁之音。伴着歌声,她们手中榔头起起落落,土坷垃纷纷应声而碎。
打完坷垃,还要再耙上一遍,这次耙地就快多了,铁齿过处,细土如面。四伯说:“地要耙得蓬松,麦苗钻出来时才省力得劲。”
土地耕耘完成了,耩麦播种就要开始了,四伯仔细检查着耧车,枣红木耧车被擦得锃光发亮,耧腿上的铁铧子闪着耀眼的寒光。
四伯手试耧铃,铃舌转动,发出清脆的“叮当”声。“铃响种子匀。”他看着我笑着说。
太阳升起来了,四伯也调试好了木耧。他到田埂上换上一件新褂子,腰里系上一条红绸布,这是寒露种麦开耧第一耧,主耧人喜庆的传统打扮。寓意着来年风调雨顺,仓箱可期,日子一定红红火火。
木耧耩麦是不用黄牛老犍的,是在木耧上系上几根长长的麻绳,大家把绳子放在肩上拽着走。
妇女们都回家做饭了,生产队长又调来几位棒小伙,大家肩披垫布,绳子搭在肩上,绷得笔直,静候开耧发令。
“开耧了!”生产队长一声吆喝,大家躬背用力,拽耧向前,耧铃便“叮叮当当”地响起来了,那清脆的铃声划破天际,在寒露的晨风中格外悦耳动听。
我跟在耧车后面溜种子,这是最轻的农活,但要格外细心。耧沟里那处种子稀疏,就要按四伯的指令补上一些。母亲嘱咐过我:“漏种一粒籽,少出一棵苗,少蘖一簇禾,欠收一捧粮。”
早晨饭时到了,妇女们送来了田头耩麦饭,红薯玉米糊,外加红薯面馍和咸菜。大家围坐在地头的空地上,一边吃,一边听四伯讲墒情:“看着土色,正是满墒,老天眷顾,耩麦正当时,早了粘耧,晚了飘籽。”
四伯一口玉米糊饭一口馍,还不住地讲那一九六零年。“记得那年寒露前后几个月不下雨,只好干耩,结果麦苗没出几棵,收成没有种子多。他说着叹了口气,咱农民靠天吃饭,难啊!今天墒好天气好,大伙别怕累,一定一鼓做气耩完地。”
下午耩地,我主动换了拉绳的活,绳子勒在肩上辣的疼,最脸红的是跟不上大家行走的节拍和耧铃声。走快了种子稀,走慢了种子密。最要命的是只顾埋头拉绳,不抬头看路,把拉绳卡在了耧腿里,麦种一下堆在了楼眼里。四伯让大家停下来休息,他用楼鉴慢慢捅开。他边捅边讲:“这是噎耧,不能横劲拉,得顺劲走,顺劲拉。”
在大家的帮教下,我终于步子走对了,劲也用顺了,肩上虽说磨出了水泡,但心里挺高兴的。
我最喜欢看四伯摇耧,他手腕灵活,像唱歌打拍子。还能从耧铃的响声中悟出下种均不均匀,耩得快了,铃声响得急,像下雨;耩得慢了,铃声就缓,像念佛。种地人的喜怒哀乐,都在这叮叮当当的耧铃里。
大阳快要下山了,田地变了模样,新耩的麦地如同一幅几何形的画卷在不断向前延伸着。微风起时,风里带着泥土麦种的混合气味,四伯说:“这就是寒露味。”
耧铃声止,二十亩的麦田我们终于耩完了,晚霞映在那片土地上,泛着琥珀色的光。
短暂的农村劳动生活以后,我参加了工作,离开了家乡,离开了那片热土,再也没有听到寒露的耧铃声。
多年以后,一次回乡探家,在村头的老仓庫里发现了那架枣红木耧。耧身已经腐朽,耧铃也锈迹重重。我轻轻一晃,似乎还能听到那熟悉的“叮当”声。这声音穿越了半个世纪的时光,依然清脆如初。
寒露又至,我再次回到乡间,站在田埂上,看着播种机在田间驰骋,效率高得惊人。喜庆之余,心中总觉得少点什么。或许就是那叮叮当当的耧铃声,还有那金秋中对土地新生命的期盼。
恍惚间,我仿佛听到那熟悉的耧铃声从岁月深处传来,这声音里,有泥土的特殊气息,有汗水的咸涩味,还有乡亲们对土地最质朴的眷恋。
也许,真正的眷恋不是耧铃本身,而是那个寒露时节播种的希望,是深植在家乡人血脉中对土地的深情。就像那些埋在土壤里的麦种,看似寂寞,却始终在酝釀着破土而出的力量。
昨晚又梦见了那片麦田,梦里耧铃声格外清脆,像是要把整个秋天都铃醒。醒来推开窗,发现今天就是寒露,远处一台播种机正在田地里轰鸣,那声音激越高亢,彰显着这个时代特有的奋进韵律。
我忽然明白,原来,渐行渐远的耧铃声从未真正消失,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,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继续回响。就像寒露时节总会如期而至,土地上总会有人播种,有人守望。
寒露节的耧铃声,不仅是一种季节农事的信号,更是一个时代的回响,它响在土地深处,响在家乡人心里,响在每一个渴望丰收的梦里。

龚广涛,南阳市作家协会会员,南阳汉文化研究会会员,南阳市卧龙区作家协会理事,南阳市卧龙区诗词楹联学会理事。作品陆续刊发于《语言文字报》《河南日报》《晚霞报》《教育时报》《南阳日报》《南阳晚报》《南阳晨报》《揭阳日报》《榆林日报》《儋州今报》《洵阳晚报》《绥化晚报》等报纸和《南阳网》《南阳市图书馆》《大河文学》《中州作家文刋》《卧龙文艺》《辽宁文学》《大连文学》《宁古塔作家》等网络媒体。